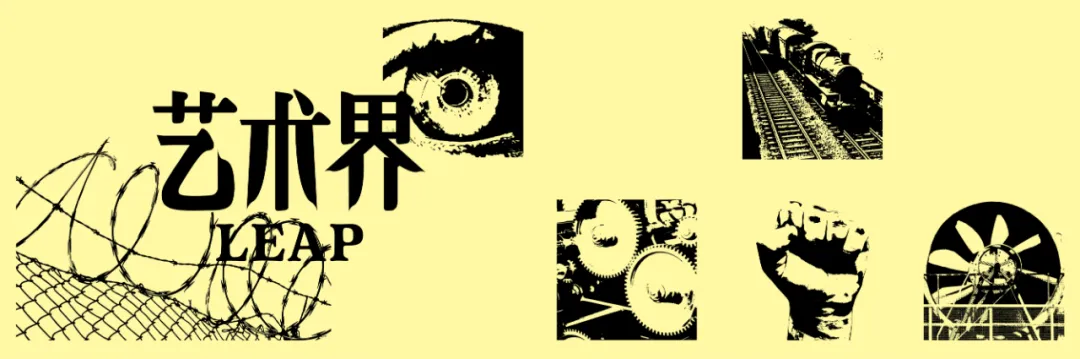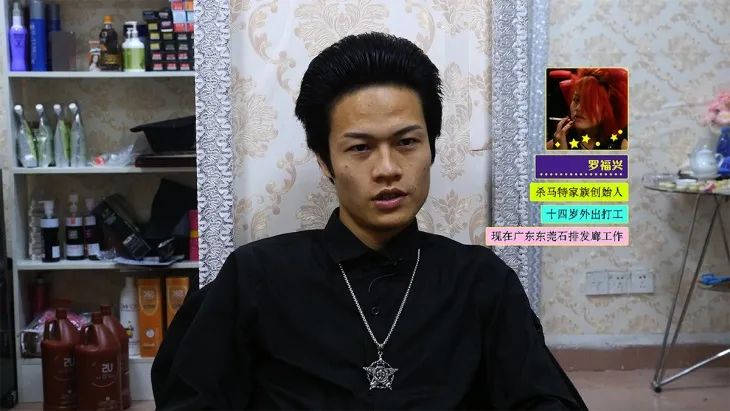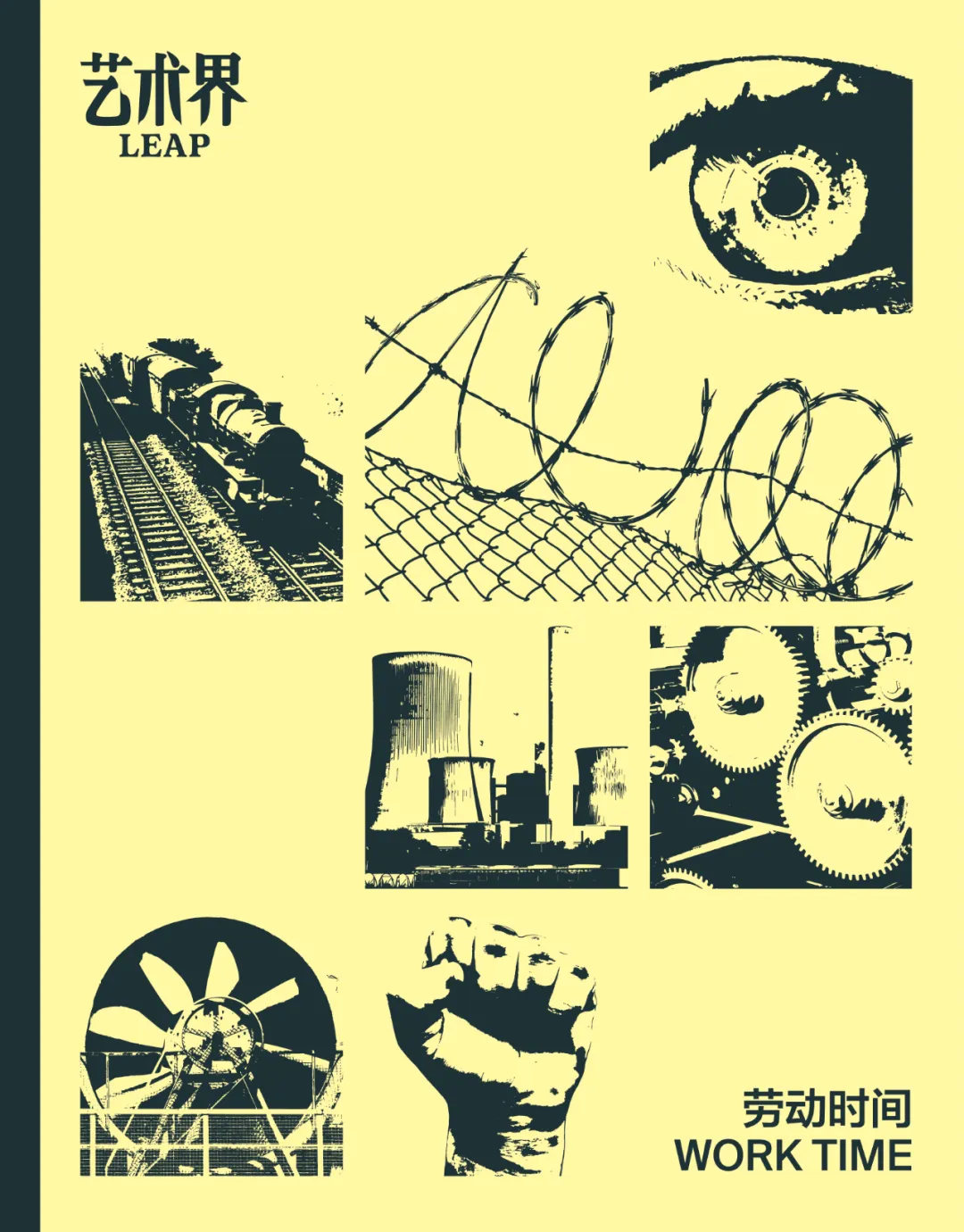劳动时间|失声“盲流”与短视频“牛马”——非虚构影像中的中国工人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艺术界LEAP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
关键词:打工人, 影像, 纪录片, 中国, 空间, 国家
涉及行业:服务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上海市, 广东省
相关议题:人口移动/流动
- 近年来,"牛马"成为了简体中文互联网语境中流行的词汇,它代表了工人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和形象,反映了对工人群体认知的变迁。
- 中国工人的非虚构影像展现了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工人到改革开放后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以及面对现代化挑战的流动工人的多重面貌。
- 独立纪录片通过聚焦于工人的日常生活和劳动环境,揭示了工人在社会变迁中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如安全问题、社会保障缺失等。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主流媒体纪录片开始关注工人个体的故事,展现下岗工人适应社会的过程,以及在社会变革中通过个人努力取得成功的案例。
- 独立纪录片揭示了城市扩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建筑工人等流动工人群体面临的权益保障不足和生活困境,强调了对这一群体更多关注和支持的必要性。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失声“盲流”与短视频“牛马”
——非虚构影像中的中国工人
Voiceless Drifters in Blindfolds
and Tik-Toking Workhorses on Reels:
Chinese Workers in Non-fiction Cinema
爱德华·伯汀斯基,《生产#18》,2005年
数码激光冲印
图片致谢Zeitgeist Films
“没有钱的人,今天也在算,一块两块也在算,明天也在算,算了一辈子还是没算到钱。”
——孙翠英,《厚街》中的女工
前几年,冰岛旅游局推出过一支解放打工人的旅游宣传视频,视频中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在快乐玩耍时突然收到工作邮件,快乐就此告结。针对“度假被打扰”的苦恼,旅游局贴心地推出“小马外包邮件(OutHorse Your Email)”服务,让冰岛马在键盘上随机行走帮游客回复邮件。视频当然十分可爱,但如果由“打工马”联想到“牛马”,看着冰岛打工马在雪山青草之间随地走动,想打字就打字,想睡觉就睡觉,打工人敏感的神经不免又要被小小地扰动一下。
简体中文互联网语境中近年风靡的“牛马”,在不过十年之前曾有另一个名字——“工人”。这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承载浓厚政治意味的词语,对于中国人而言从不陌生。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叙事里伴随资本主义工厂崛起而失地、被迫进入工厂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形象,中国工人在不同时代形象不尽相同。计划经济时代东北、两湖等地国有企业的工人,在国家话语中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国家建设的先锋,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和“铁饭碗”;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摆脱户籍制度束缚奔向城市务工的人,被称为“农民工”,以“暂住证”区别于城市户口居民;另一个带有浓重时代色彩的词是“盲流”,伴随这个词汇而来的,往往是大规模的“集中安置”或“治安管理”。对工人称呼的几经易转,折射出中国主流社会对工人群体的认知变迁。同样,非虚构影像对中国工人的表现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可以看做这种认知变迁的视觉化。
相比世界影像史的试水开山之作——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La Sortie de l'Usine Lumière à Lyon, 1895)出现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19世纪,工厂尚被视为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新世界朝气蓬勃的象征,20世纪的工厂已在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中成为剩余价值剥削的代名词,中国工人的非虚构影像亦在这与压迫斗争到底的时代浪潮中涌现。1925年,我国纪录片史上第一部“工人纪录片”《五卅沪潮》(1925)就诞生于反殖民、争取工人权益的五卅运动。影片由友联公司的陈铿然与徐琴芳、刘亮禅拍摄,呈现五卅运动期间上海工人罢工抗议情形,重笔记叙工人运动遭到殖民者暴力镇压的惨案。该片同年6月在上海公映,票房收入全部用以接济罢工工人。[1]同一时期,苏联导演B·A·史涅伊吉洛夫亦在上海、广州拍摄了纱厂工人劳动、工人群众大会情形和广东工人近卫队训练场景,剪辑成纪录片,命名为《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国内战争》(1925),后更名为《东方之光》。[2]
值得一提的是,与西方表现工人的影像常建构出资本家与工人、国家与个体权益的二元矛盾框架不同,中国的近代史同时也是工人阶级政党崛起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人影像并非纯粹的“边缘”范畴,与“工人”概念在国家革命与建设初期被赋予的特殊主体意义、在改革之后被列入不同的社会分类一致,工人影像常年游走于国家叙事与民间叙事之间,二者在某些时期甚至是重叠的。如20世纪20年代后部分工人纪录片逐步转向剧情化,发展出30年代如《女性的呐喊》(1933)等一批后被称为中国“左翼电影”的工人虚构影像。在这一类影像的生产过程中,试图推动国家变革的文化精英与底层劳工的立场高度重合,工人既是影像的表现对象,又是影像生产与传播的主体,推动了自下而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
而在社会主义改造与长达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群体更是在对国家共同体未来图景想象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新的国家建设蓝图的支柱。中国电影史学者方方将1949年至1983年称为中国纪录片的“英雄时代”,寓指在物质匮乏、技术受限的情况下,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纪录影像都被用以讴歌英雄与记录社会主义建设成就。[3]公私合营后,制片厂均成为国营单位。这一时期的工人纪录影像代表了国家意志,如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三八”妇女带电作业班》(1974),主要内容是女电线工人英勇挑战高危工作。[4]在这类影像中,工人被视为国家理想主义的化身,以英雄面貌出现在非虚构影像中,也无形之间被虚构,浓缩为高度抽象的英雄符号。
当经济体制改革开始,20世纪90年代的主流媒体纪录片亦开始转向对个体故事的叙述,如1998年湖北电视台拍摄的《四姐》与2002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张希永》,均描述下岗工人重新适应社会。近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国工匠》(2015)系列纪录片亦依然延续这一脉络,强调社会变革下个体通过个人努力取得成功,试图将被体制改革抛出旧有轨道的工人重新整合进新的国家发展叙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主流媒体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奉行的价值体系与美学不存在分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二十世纪末期,随着DV摄影机流行,中国独立纪录片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在主流媒体机构的大型摄影机无法压低镜头看见的角落,独立纪录片人携带轻便的小型设备进入工厂与工地,将镜头对准不符合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话语中“工人”形象的普通工人,把他们的日常生活作为表现对象。
上图:《人造风景》(2006)纪录片中展现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镜头下受工业化影响的环境变迁。
爱德华·伯汀斯基,《三峡大坝工程:奉节#5》,2002年
数码激光冲印
图片致谢Zeitgeist Films
下图:王兵,“遗存的影像”系列(摄于铁西区)
1994—2001年,摄影,共102张
致谢艺术家和魔金石空间
20世纪末21世纪初独立纪录片的工人影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回归故土与乡镇,关注国有企业改革后原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境况,如林鑫的《三里洞》(2007)《瓦斯》(2011)呈现家乡父辈矿工群像,摄影机如幽灵,徘徊于已经废弃的矿厂,跟随采矿车进入矿坑,仿佛在无声追问逝去的时代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一幕也使人想起《铁西区》长达2小时的空镜,工业时代谢幕的景观在不同观者眼里大概有不同色彩;于广义的《木帮》(2006)开展于严酷的东北寒冬,伐木工人既是森林的外来者,代表工业对自然的入侵,又早已与兴安岭的茫茫长夜融为一体。他们像山林的原住民一样相信大神,生病时求助于萨满;当他们死去,森林的树木作舟,运载他们的身体回到山上。他们似乎在体制之内,又似乎在体制之外。
另一类追随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方向,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国西部到东部,聚焦于在城市务工的流动工人。正如摄影集和纪录片《人造风景》(2006)强有力的隐喻断言“中国的现代化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轨迹,如同改变这个国度的风景”[5],在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变化之中,城乡流动带来的断裂景观是最为显著的一种,“流动人口问题”也成为21世纪初中国最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民工在其工作的城市难以享有与城市户口居民同等的权益,这一点在建筑工人身上尤为突出。城市的飞速扩展带来大量建筑用工需求,但相应的劳动保障并未能及时匹配,胡杰的农民工系列纪录短片《拆房工》(1997)与《架子工》(1998)即在90年代末奏响了城市交响曲的一个杂音,《架子工》影片开头是今天知乎叙述体常见的“我有一个朋友”,而今我们都已经了然,这个朋友可以是任何人。在短片中,“朋友”是告别妻子和老母亲去南京爬架子的小郑,妻子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他能找到一份平地的工作,但小郑在空中甚至没有安全绳;“朋友”也是二十岁瞒着父母去打工的小沈,晚上蜷曲在不足一米宽的小床上。《拆房工》则不仅呈现建筑工人团体常见的“包工头”通过同乡纽带组建建筑队的模式,也呈现了民工家庭性别结构——工人往往以家庭为单位进城务工,包工头的妻子要兼顾为男性工人们做大锅饭的任务。
德勒兹主张游牧者的流动会消解空间的层级结构,建立对于个体而言更自由的新的平滑空间,“游牧的战士与流动的工人”沿着一致的逃逸路线。[6]但也正因于此,人的流动一定会遭遇已有结构的监控与限制。对于流入地政府而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显然会带来治安和管理的新挑战。一些纪录片导演以“流动”表现流动,如范立欣的《归途列车》(2009),摄影机跟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移动。另一些纪录片则以“不动”的空间呈现流动。如周浩的《厚街》(2002),摄影机始终停留在东莞的城中村三屯村,大多数镜头甚至都是在同一间名为“4432出租屋”的地点中完成的,但镜头下的人始终在变,工人们在这里暂时落脚安身,又迅速投向下一个落脚点,厚街也被城市管理者视为违法犯罪的温床;戚小光的《女子宿舍》(2010)同样对准一个两元旅馆,其初代居民是遭遇家暴出走农村的女性工人,旅馆楼下就是劳动力市场,这使得这个狭窄的旅馆成为了农村女性由传统乡土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的过渡空间。但正如郝景芳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北京折叠》(2012)所书写的隐形空间壁垒,这些女工来来去去,始终无法完全摆脱这个过渡空间,正如她们在社会空间分区的夹缝地位,看似已经脱离乡土社会的束缚,却也无法仅靠有限的打工收入融入城市。
上图:周浩,《厚街》,2022年
纪录片,55分钟
图片致谢周浩
下图:范立欣,《归途列车》,2009年
纪录片,87分钟
图片致谢EyeSteelFilm
从这个层面看,说物理空间的平移可以对抗资本与权力媾连的空间生产是太过乐观了。在一条感慨自己在广州住城中村、一天只吃一顿饭的帖子评论区中,有人称“真羡慕这代打工人。街上不查暂住证,保安也不打人,报纸也不叫你盲流,关键是还有机会上社交平台诉苦”,遭到其他网友反驳。透视争论,依稀可见两代工人境况的变与不变:21世纪初以来,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异地务工者的部分基础权利,如子女受教育权有了相应政策保障,清影工作室拍摄的《风起前的蒲公英》(2023)就记录了一所“打工人子女”学校的故事。未改变的是人口减少并未能成功倒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制造业工厂生产环境依然恶劣,新兴的技术反为“打工人”增添新的困境:平台借外包逃避对工人履行劳动保护责任,电商企业签订霸王合同让劳工自愿加班……当经济上升期的红利行将耗尽,网易新闻已被下架的纪录片《如此打工30年》(2024)折射社会流动停滞的隐痛,大约为数不多让人欣慰的一个变化是:打工人的后代不再沉默。当新时代的“打工人”反驳如段首的言论,他们所论述的事实大多并不难在网络短视频中找到证据。
新技术带来了另一种在影像空间中逃逸的可能性。如果DV摄影机尚有一定的技术与经济门槛,自带摄像功能的智能手机与短视频平台则进一步减少了民间影像参与的障碍。与在传统媒体世界中普遍失声、需要借媒体和专业人士代为发声的父辈不同,当代中国工人活跃于短视频平台,拍摄下大量自己日常工作生活的影像。一些纪录片导演以“众包(crowdsourcing)”形式与年轻工人合作,如《杀马特我爱你》(2019)收购了915段工人自己拍摄的流水线视频,更立体地呈现了顶着夸张发型的年轻工人的生活世界。如果虚构电影中出现的底层工人常是抽着烟蹲在墙角的中年男性形象,在《杀马特我爱你》中,我们看到的是脸上的婴儿肥都尚未褪尽的少年工人,通过嚼槟榔抵御长时间夜班的瞌睡。香烟和咖啡对他们来说都太奢侈了,另类的“杀马特发型”是所剩无几能被张扬的青春。
李一凡,《杀马特我爱你》,2019年
纪录片,125分钟
图片致谢李一凡
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制作的UGC纪录片《烟火人间》(2020)则因其院线取向,表现手法要更为温和一些。该片使用509位短视频平台用户创作的竖屏短视频剪辑而成,不同于《杀马特我爱你》的直白,《烟火人间》试图通过二次剪辑编织出“日常生活的诗意”,搬水泥袋的工人被联想为在起跑线上即将起身的运动健将,爬上高架举起手的女工和举起的奥运火炬图像同屏放置。赞赏者称赞其为“劳动者之歌”,以“试图创造正向、积极的情感激励而非通过刺痛感来进行社会剖析”,但同样有尊重普通劳动者的人文关怀[7];批评者则认为其过度浪漫化劳工生活,有消费劳动者之嫌。继《城市梦》(2019)之后,我们再次在主流荧幕上看见文化精英创作者融合底层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尝试。但不同的是,由于掌镜者已然不同,浪漫滤镜不会遮挡背后现实生活的底片,工人的创作、表达,以及他们创作的影片被推到大银幕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带来了更多新的可能性。
几乎同一时期,“工人”一词的严肃性也逐渐被消解,更多停留在学术研究与法律领域。新一代工人常常以“打工人”“牛马”戏谑自居。以“打工人”为关键词,可以在抖音与小红书检索到大量工人拍摄自身生活的影片和内容,其中也不乏传统意义上被称为“白领”的脑力工作者的创作内容。社会保障缺失与普遍过劳模糊了传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社会阶层界限,大学毕业生亦很难找到高收入和有保障的工作,于是自嘲式地将自己也鉴定为“打工人”或“牛马”。
孙虹,《烟火人间》,2020年
纪录片,82分钟
图片致谢大象点映
当各阶层的“工人”都加入到了“打工创作”中,短视频平台上广泛的影像参与已经脱离传统纪录片对一个或几个核心创作者的依赖,甚至不同于需要文化精英发起与推动的社区影像赋能行动,你无法陈列“典型”创作者和他们的代表作,因为它对于当代的完整勾描是建立在无数个体片段式的纪录上的——从外卖骑手的自拍,到建筑工地、厂房的日常纪录,远离家乡的维吾尔工人在海边播放思念家人的歌曲,手脚架下的苗族工人在微信群里对山歌,还有本不被看见的家务劳动,在我们面前的小小荧光屏上一一浮现。与其说这些视频碎片是年轻工人作为“自为”群体自觉自发的记录行动,不如说这是工业化机器碾压下个体抵挡被异化命运的微弱闪光,但它们无疑构成了今日中国工人生命史的“另类档案”(alternative archive)。也许对于今天关注工人影像、想要为时代修史的纪录片人而言,重要的已不仅仅是携带摄影机进入工厂,而是如何钩沉与保护这些档案,让它们越过算法的藩篱,被更多人看见。
注释:
[1] 方方,《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第40-43页。
[2] 同上,第58-61页。
[3] 同上,见第177页。
[4] 《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简史》,刘国典编,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34-141页。
[5] Zhang Xiaodan, “A Path to Modernization: A Review of Documentaries on Migration and Migrant Labor in China,”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2010, p.174-189.
[6] 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582页。
[7] 詹庆生,《在全民影像时代,【烟火人间】做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影像实验》,《北青艺评》,2024年1月29日。
文|侬那
侬那是一位无业游民,影视人类学学生,民族志纪录片拍摄者。
LEAP《艺术界》2024年秋冬刊“劳动时间”
现已上架,点击“阅读原文”购买
香港及国际订购
Hong Kong and international purchase, email:
作者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
© LEAP |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联络邮箱:[email protected]